
随着一阵急刹车的声音,苏丹被迎面驶来的车子撞飞了出去,她感觉自己在天上飞,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大床上,床的旁边是漆着原木纹理的一个组合柜。组合柜旁边是一个五斗橱,用来装粮食的,床的正对面是一个大窗户,正午的阳光正照在这个屋子里,把这个小小的屋子照的温暖无比。

明德六年八月十五,皇帝大婚,迎娶沈盖将军之女沈若蓝为后,天下大赦,举国同庆。 太和殿里金碧辉煌,喜气洋洋。 他掀开我的红盖头,红烛将他棱角分明的俊朗脸庞衬得分外柔和,剑眉下的凤眼闪着光芒,薄唇轻启:“蓝儿。。。。。。我终是娶到你了。”

夜,月色很好! 七王府内,除了偶尔巡逻的家丁走过的声音,寂静无声。一个黑影突然掠过,却引起一阵骚动…… 他正在案前读书。在明珠通明的室内,他面色沉静,皮肤白皙胜雪,高耸挺立的鼻子如同天公雕刻一般无可挑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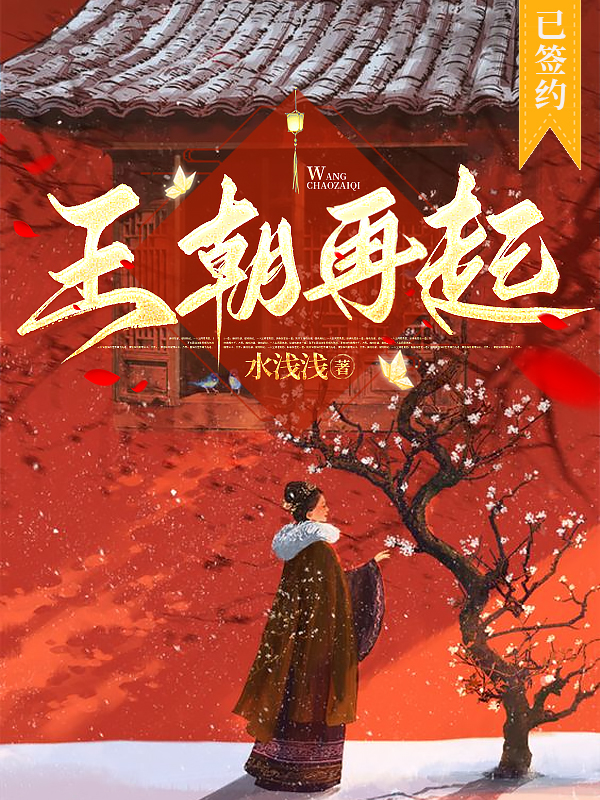
夏苍大陆迎来了又一个黎明,西方落下的太阳又从东方苍穹升起。 人们照旧听到鸡鸣的声音从混沌的梦境之中清醒过来,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,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,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。他们只知道听从自然的命令

守望麦田
穿梭在城市角落,夏落始终迷茫着,似乎看不清前面的方向,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,眼前似乎没有了路可走。繁华的都市并没有引起她一丝一毫的兴趣,她唯一在意的那个人是不要她了,还是不要了这一世笑话。 拉着一个行李箱,看着周围车水马龙,夏落显得格格不入——是来错了这个世界还是不想融入这个世界。她想要去的世界有他就足够了。虽然那人一直很忙,尤其是在他大学毕业后甚少陪她,尽管如此,夏落还是很满足,觉得很幸福,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,从此她就是他妻子,不离不弃。


守望麦田
穿梭在城市角落,夏落始终迷茫着,似乎看不清前面的方向,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,眼前似乎没有了路可走。繁华的都市并没有引起她一丝一毫的兴趣,她唯一在意的那个人是不要她了,还是不要了这一世笑话。 拉着一个行李箱,看着周围车水马龙,夏落显得格格不入——是来错了这个世界还是不想融入这个世界。她想要去的世界有他就足够了。虽然那人一直很忙,尤其是在他大学毕业后甚少陪她,尽管如此,夏落还是很满足,觉得很幸福,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,从此她就是他妻子,不离不弃。


随着一阵急刹车的声音,苏丹被迎面驶来的车子撞飞了出去,她感觉自己在天上飞,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大床上,床的旁边是漆着原木纹理的一个组合柜。组合柜旁边是一个五斗橱,用来装粮食的,床的正对面是一个大窗户,正午的阳光正照在这个屋子里,把这个小小的屋子照的温暖无比。

在遥远的南方,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,有一个村庄,名无明! 村庄不大,统共也就几十户人家。 不过,背景都不简单,大多是,千百年传承的官宦富贵人家。 村里有一条河,名若水此河四季水瞒,春暖夏凉,清澈见底。

云缭雾绕的少室山门前,一位丰神俊朗的中年男子负手而立,墨玉般的眼眸深不见底,随意地看着远处,不知在思量着什么。猎猎山风吹的他一身白衣作响,也毫无所觉,直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沙弥走近时,他才拉回了神思。

数不尽的苗疆风云,道不尽的儿女长情。唱一首离歌,悯一代佳人。 一副画,两个争;一座桥,架云峰;城水流,鱼雁醒;琴箫合,青鸟鸣。 相远望,目濛濛;遥相思,泪成行;寄兰草,诉情笼;梦里兮,皆迷红。 登台而望苗山月,夜夜思君万里情。 满院雪花川簌落,失眠不见马蹄声。

时间不详,地点不详,没准你会嘲笑“这还活个什么劲啊!” “笑吧,我还能说什?但当你知道我得经历,也许你可以试着沉思!” 昏暗的灯光,钢铁的牢笼。两个壮汉肩背AK-47冲锋枪,蒙着面大步走来。声音越来越近,戛然而止。 停在了我得“房前”! 只听“吱呀”声不绝,让人牙酸,门开了!

又是一年春节。顾文启坐在舒适的车座上,闭着眼假寐着。司机开得很稳,可他就是睡不着,心里又期待又害怕。 今天是大年初五。往年的今天,许陶一都会赶到顾家拜年。顾文启的父亲是非常喜欢许陶一的。这个戎马一生,不拘言笑的师长,只宠溺包容的就是许家的三姐妹。其中对许陶一更甚。 只是……整整两年许陶一都未踏进过顾家老宅一步。顾文启明知今年也会以失望告终,还是忍不住推掉一切重要的工作和应酬赶回H市。希望今年可以看到那张眉眼弯弯的笑脸……

白君唯皱了皱眉,有些不悦:“你说什么?!” 墨倾珏打了个机灵,“额,啊?你刚才说什么……对了,小叔叔还等着下酒菜呢!”说着趁白君唯不注意,赶紧往外跑。 白君唯顿时气结,看着墨倾珏仓皇跑了出去,又是满心的无奈。片刻后,他伸出指尖优雅的抹掉嘴角的药汁,微微一笑“小倾儿,反正你也逃不了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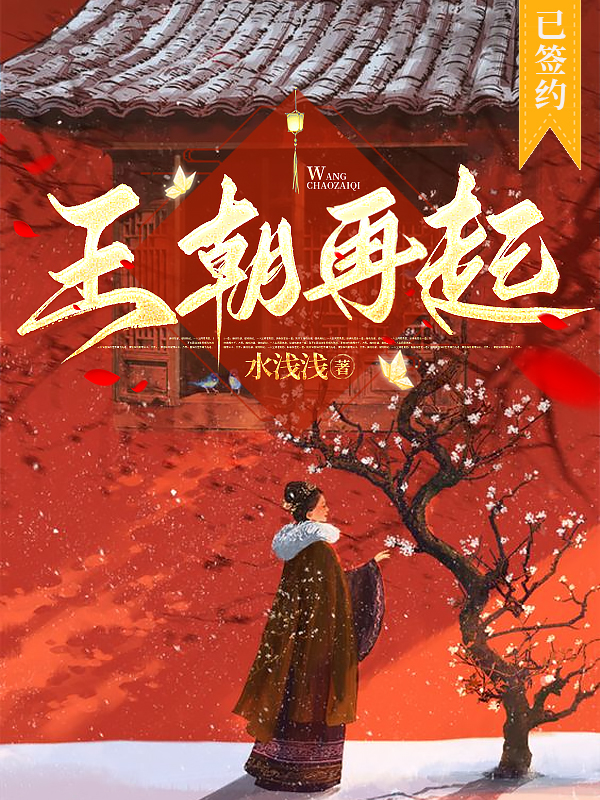
夏苍大陆迎来了又一个黎明,西方落下的太阳又从东方苍穹升起。 人们照旧听到鸡鸣的声音从混沌的梦境之中清醒过来,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,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,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。他们只知道听从自然的命令

我回谷的那日,正是雪下得大,我正咒这见鬼的天气冷得太过时,见轻辰君立在我面前,他,他,他他似乎有些生气?一双锦绣的眉蹙成“川”字,见着我,咬牙切齿:“云雪见,这几百年你死去了哪里?” 记忆中的轻辰君是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,他他他为什么动如此大的火气?我有些惊愕,但也不好将他晾在外头,遂请他进屋去细说。